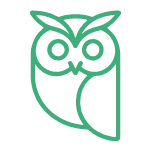“纯正的趣味”:朱光潜的批评标准
- 作品研究
- 2022-09-30
- 213热度
- 0评论
在朱光潜看来, “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如果说创作是作者的情趣与表现对象的情趣之间相互斗争、磨合,那么欣赏则是读者的趣味与作品中体现的作者的趣味之间的较量。读者的趣味和作者的趣味必不相同,这样较量才有价值,“创造的批评”才有可能。
在朱光潜看来,文学是人生世相的返照,人生世相杂乱不堪,变动不居,诗人于是取舍剪裁,并熔铸自己的情趣性格,另创出一个独立自足的新宇宙。文学所创的新宇宙是一个“不即不离”的境界: “不即”者,不是对现实经验的机械复制,所以新鲜有趣; “不离”者,不完全脱离现实经验,所以不同于空中楼阁。而无论是欣赏还是创造,都必须见到诗的此种境界。如何见到这种境界呢?朱光潜认为要点有二,一是对形象的直觉,二是形象与情趣的融合。
朱光潜认为诗歌境界的产生必须依赖对形象的直觉。他用观察梅花的两种态度说明了直觉即表现。我们面对一株梅花,产生“这是梅花”、“这是冬天开花的木本植物”、“它可以用来插花”等等想法,这都是对梅花与其他事物关系的知觉,我们得出的都是梅花在与其他事物相关联中产生的“意义”,而非梅花本身的意义,这就是对梅花的逻辑的、概念的把握。此外,当我们凝神注视梅花的形象本身,就会无暇思索梅花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显出的意义,这时对梅花的把握就是对梅花自身形象的直觉,所觉的就是梅花本身形象在我们心中显现出的意象。朱光潜进而指出:“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
对诗歌完整的境界的把握必须依靠形象的直觉。但是“名理的知”(思考、联想等)不能被完全抛弃,它们是一种酝酿工作。我们通过艰苦的思索和联想,才有可能豁然开朗,对诗的境界达到总体的、完满的把握。总之,境界的产生首先要在直觉中形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如果一首诗没有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就犯了芜杂拼凑的毛病,也就谈不上有境界了。
此外,要产生诗的境界,直觉到的意象必要恰好表现作者的情趣。朱光潜对意象和情趣相互契合的过程加以描述: “凝神观照之际,心中只有一个完整的孤立的意象,无比较,无分析,无旁涉,结果常致物我由两忘而同一,我的情趣与物的意态遂往复交流,不知不觉之中人情与物理互相渗透。”情趣和意象相生相合,就产生诗的境界。朱光潜将“情趣”简称为“情”,“意象”即是“景”,于是诗的境界便是情景的契合: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从“创造的批评”的角度来看,朱光潜认为就见到情景契合的境界来说,欣赏和创造没有分别。作家见到一种境界,感到它有情趣,这是用一种欣赏的态度对待他见到的境界,进而借助文字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他是在创造也是在欣赏。读者从作者的文字符号中领会出作者体验到的境界所依据的也是同一种“心灵综合作用”,所以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明确了情趣和意象相契合的关系,朱光潜进而探讨了王国维作为批评标准的境界理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朱光潜认为王氏的“有我之境”是移情作用的结果,而移情作用必须的是凝神关注,物我两忘,所以“有我之境”实际上是“无我之境”;而“无我之境”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是诗人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妙境(华兹华斯语),所以实际上是“有我之境”。但是严格说来,“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所以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不如题为“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
可见,朱光潜是用自己意象、情趣相契合的理想境界标准,重新诠释了王国维的境界理论,自成一家之言。从诗歌意象和情趣之间的关系出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学趣味”。因为,“赏识‘郴江绕郴山’的是一种胸襟,赏识‘孤馆闭春寒’的另是一种胸襟;同时,在这一两首词中所用的鉴别的眼光可以应用来鉴别一切文艺作品,显出同样的抉择,同样的好恶,所以对一章一句的欣赏大可以见出一个人的一般文学趣味。”
(江守义,刘欣)